加林加林是什么歌公元7世纪中叶东亚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巨变。这场巨变改变了东亚各国的版图,重塑了东亚的国际关系,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中国大陆上大唐王朝逐渐扫平隋末群雄之际朝鲜半岛正在上演“三国演义”的剧目:高句丽占据着现在的朝鲜以及中国的辽东半岛,而百济和新罗则分据现在的韩国。这里需要说明:高句丽其实并不是朝鲜半岛的本土政权,而是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是在遭受曹魏打击后才逐渐把统治中心迁往朝鲜半岛,如今高句丽的王陵仍留存于我国境内。百济其实同样不是半岛本土政权,而是和高句丽一样是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扶余民族的后裔。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和我国的三国时代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魏、蜀、吴都是直接脱胎于汉王朝的同一民族政权,然而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所以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仅仅只是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方博弈的格局态势。
三国中高句丽从隋朝起就引起了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正如上文所言:高句丽并非半岛本土政权,所以从一开始高句丽就呈现出与后来朝鲜半岛上的新罗、高丽、李氏朝鲜等王朝完全不同的特征。朝鲜半岛后来的王朝都属于内敛型王朝,给人以文弱之感。然而高句丽却极为强悍:南北朝时期高句丽趁中原混战之机占据了辽东半岛,隋朝在完成南北统一后就一直设法收回此地。辽东半岛位于东北的关键地区——距离契丹、奚等部族的核心区很近,是战略上的制高点。隋炀帝为取得辽东半岛曾三征高句丽,然而战争所带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与隋炀帝在国内搞的各种大型工程一起构成了压垮隋朝的沉重负担。辽东半岛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而控制此地的高句丽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游牧渔猎民族,事实上高句丽是一个兼具游牧渔猎民族的勇武彪悍且高度汉化的民族。单纯的游牧渔猎民族虽勇武彪悍,然而经济文化过于落后而无法与中原王朝抗衡;相比之下后来朝鲜半岛上高度汉化的王朝却又丧失了勇武之风;而像高句丽这种兼具双重特点的民族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匈奴、突厥这样纯粹的游牧民族无法统治中原,而兼具游牧民族的勇悍又效法中原汉制的辽、金、元就可以实现对中原王朝的压制呢?原因正在于此。正因为高句丽的这种特征使其注定被中原王朝视为大敌。尽管已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然而号称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依然义无反顾踏上了东征高句丽的路途。
李世民没像隋炀帝那样一败涂地:他成功拿下了高句丽周边的外围据点,然而并没实现全取高句丽的既定战略目标。高句丽为何如此难打?主要还是地理交通问题:从隋唐边境到高句丽都城平壤是一个上千里的巨大弧线,中间需要经过巨大的沼泽地带,后勤补给极为困难。隋唐王朝每次出征看似兵强马壮,然而大量人力物力都消耗在漫长的战线上了,等真到了战场上实际已没剩多少战斗力了。隋唐王朝屡屡东征高句丽却未能实现战略目标的现实使半岛南部的百济也渐渐开始对大唐王朝有了轻视之心。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正值唐太宗李世民用兵高句丽时期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国在有“海东曾子”之称的国王扶余义慈领导下联合高句丽出兵进攻新罗,夺取新罗四十余座城池,尤其是战略要地棠项城的陷落从此阻绝了新罗向唐进贡的陆上通道,危急万分之中的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小龙虾。恰巧此时大唐西北的西突厥又和大唐发生冲突,忙于西北战事的李世民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百济进行警告。百济对大唐的警告置若罔闻:不仅又攻占了新罗十几座城池,还断绝了向大唐朝贡。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百济重新遣使向唐朝进贡,然而李治已对百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大为光火。
李治给百济国王下发诏书称: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勿谓言之不预也。尽管这份诏书的措辞已相当严厉,但百济朝廷并未将其当回事——在他们看来:百济与唐朝陆路不通,两者之间隔着连隋炀帝、唐太宗都未能平定的高句丽;而海路方面:今天的黄海在当时看来几乎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军事屏障。依然我行我素的百济于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与高句丽达成战略默契: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新罗。自知不敌的新罗只得再度向大唐帝国求救。唐朝这次已不打算再警告百济和高句丽,而是派出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试图从陆上减轻新罗的军事压力。在这场战斗中唐军大破高句丽军队,杀获千余人,但由于所派兵力不足,新罗的危机并没解除。其实此时的唐朝也有难言之隐——太宗晚年就已爆发的和西突厥的战争还在继续,唐朝无法全力应对东北战区。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正月初二唐军在苏定方率领下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压力缓和下来,这使李治得以将苏定方的军队调往东北和高句丽、百济对阵。
公元660年5月刚于四个月前在西北战胜西突厥的苏定方率部渡海向百济发起进攻,并于6月下旬抵达今天的仁川附近。与此同时新罗国王金春秋亲自率兵出京城(今韩国庆州),最终成功和作为友军的苏定方部在仁川附近回合。苏定方和新罗太子金法敏约定:唐军由海路,新罗军由陆路分头进发,于7月10日会师合围百济都城泗沘。面对十八万唐罗联军,慌乱中的百济朝廷临时匆忙组织起力量在白江口处和沉岘(今韩国大田市西南)以步兵阻击。苏定方顺利击溃前来阻击的百济先头阻击部队,在距离泗沘城数十里的地方与百济主力部队展开角逐,唐军大破敌阵。新罗军方面一度进攻受阻,导致其与唐军会师的时间比预定晚了两天,引起苏定方大怒。不过这一历史细节并没影响整个战争的进程:两军回合后开始部署阵地合围泗沘。第二天即7月13日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弃城而逃,留在泗沘城中的王子扶余泰趁机自立为王。扶余泰只是百济王族中一名普通王子而并非太子,太子扶余隆之子扶余文思此时尚在泗沘城内,他担心扶余泰对自己下手。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扶余文思率先缒城向唐军投降。四围重兵压城之际国王扶余义慈弃城而逃、太子之子扶余文思率先投诚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时间百济方面降将如潮。扶余泰被迫率领文武百官请降,百济都城泗沘陷落。7月18日逃到熊津城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率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面的部队请降。自3月10日唐高宗李治下发远征百济的诏书到8月12日平定百济的捷报传回大唐京城前后五个月时间内割据海东近五百年之久的古国百济就灰飞烟灭了。然而就在百济国王扶余义慈投降后不久百济旧地就先后涌现出几支反叛力量:他们退守南部的南岑、真岘(今韩国大田市附近)等城,或与唐军和新罗军形成静态对峙局面,或频繁进行小股骚扰。
叛军中的一支是以原百济将领黑齿常之为首的兵民合体势力。这本是一支不该出现的叛军——黑齿常之在百济朝廷投降后也率部投诚并前往泗沘城向唐罗联军送款。然而苏定方在战胜后放纵士兵劫掠,引起民愤。黑齿常之在惧怕之余利用当地民意率十余名亲信遁归本部,纠结亡散,形成以任存山区为基地的军事堡垒。他们结栅自保,旬月之间收留了百济残众三万余人。8月26日苏定方遣兵攻打,因任存山地势险要,唐罗联军没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进展。从黑齿常之战后初期的投诚行为来看:他并没太强的反叛野心;从他此后的军事动作来看: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于固守任存山,并没对唐军发起主动进攻。这实际上是一支处于观望中的兵民杂糅力量,如果唐军能成功平定其他叛军,这支军队会主动归顺。另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则相对棘手: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3月僧人道琛自称领军将军,鬼室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诱各地叛军,势力迅速扩张。这股势力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境内)并在泗沘城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试图围困泗沘城里的唐罗守军。与此同时这支叛军还向日本寻求援助,于是日本方面授予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织冠阶并将一名日本贵族女子许配给他,随后又正式册立其为百济王,派出日军五千余人、战舰一百七十艘护送其返回百济旧地,由此日本加入到干预百济战事的活动中。
在那个年代整个东亚都是中国的弟子,而朝鲜半岛则是日本的师兄。几百年间朝鲜半岛一直扮演着中日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角色: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刺激下日本才由一个个四分五裂的原始部族进化为一个统一成熟的国家。当时的日本称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迁徙来的人为渡来人,这些人给日本带来了语言文化传统。日本相对比较优待这些人因为日本朝廷比较看重这些文化和知识。815年日本朝廷编写了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的姓氏:1182个统治阶级姓氏宗族里205个来自中国(包括高句丽姓氏41个),154个来自朝鲜半岛(百济104,新罗9)。与此同时水稻种植技术也开始在日本日益普及——西元前3世纪以后水稻迅速在日本列岛传播开来。水稻、铁器、文字、宗教都是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如果没朝鲜半岛的输入,那么日本能否建国都将是个问题。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大和朝廷出兵朝鲜半岛,征服了所谓“弁韩之地”并在此设“任那府”进行统治,半岛上的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日本的佛教就是由百济传入的,甚至连日本的明仁天皇也在68岁生日的当天承认桓武天皇的母亲来自百济王室家族。日本尽管一直通过朝鲜半岛学习中华文明,然而日本在心理上却认为自己的地位理应位居朝鲜半岛之上。在我国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当时的倭国王曾遣使要求刘宋朝廷册封自己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当时日本这种请求中国朝廷册封的举动说明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这时的日本是不敢将中国确定为自己侵略扩张的目标的,事实上这时的日本是承认东亚世界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所以才会有请求中国朝廷册封之举;尽管这时的日本是臣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但从日本的请求册封之举中也能看出这时的日本实际上已萌发了大陆情结,因为如果当时的刘宋朝廷满足了日本的册封请求就意味着中国朝廷承认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等地为日本的属地。这就是日本当时的野心:在承认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之下自己要扮演该体系内仅次于中国的大国角色,也就是说日本要求对其他小国拥有支配权。不过刘宋朝廷最终只册封倭国王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也就是说刘宋朝廷并没认可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倭国与百济、新罗等国一样是中国朝廷的藩属国,彼此之间属于平等关系。
日本的诉求没能得到当时的中国朝廷的认可,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混战时期,日本趁中原王朝无暇顾及域外事务的时机扩张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最终日本实际上迫使百济成为了自己的朝贡国,不过此事一直没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随着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张使其野心逐渐膨胀,于是到了隋炀帝在位时期就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这份国书标志着日本正式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发起挑战:在此之前日本尽管已在朝鲜半岛展开扩张行为,然而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是认可的,所以才会请求册封之举。以隋炀帝时期的国书事件为标志宣告日本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在当时的宗藩朝贡体系之下只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被视为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也只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能成为皇帝,周边藩国的统治者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然而日本统治者的名号却在这时由原来的大王悄然变成了天皇并在国书中以天子自居。日本尽管国力还比较弱,然而在心态上已完全把自己放到和中国隋唐王朝对等的位置上,而这是新罗、百济等国均未曾做过的。所以当百济事变发生时日本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决定利用此事彰显自己的存在感:齐明天皇摆出了御驾亲征的姿态,同时命令北九州地区集结军队。谁知齐明天皇刚赶到北九州就病死在筑紫朝仓宫。她的继承者放弃了亲征计划,但还是决定权力援助百济复国军。
然而百济叛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僧人道琛和鬼室福信眼中从日本送回的扶余丰仅仅只是作为王室的代表以加强队伍的影响力、号召力,他们自然不愿分权给扶余丰,而道琛和鬼室福信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这时作为大唐检校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刚赴任百济的刘仁轨利用百济叛军内部的矛盾向道琛和鬼室福信陈说利害、慰谕招降。道琛不愿就范,鬼室福信便杀害了支持复国运动的主要人物道琛和尚,转向背叛扶余丰的一边,并密谋将之杀害。扶余丰也早已开始猜忌鬼室福信,于是公元663年6月在日本协助下拘捕鬼室福信并将其处死,自此百济残军的指挥大权完全落在日本册封的百济王扶余丰手中。百济叛军的内讧给唐军的军事部署创造了条件:又一支唐军在孙仁师率领下渡海而来和刘仁愿、刘仁轨部会师。作为盟军的新罗军队在其太子金法闵率领下也在七八月之交顺利和唐军会合。这时众将讨论进攻目标——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道,何不首先攻打它?”刘仁轨说:“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巢,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绝大多数唐军将领打算先攻打作为水陆交通要冲的加林城,而刘仁轨始终坚持绕开沿途一切水陆重镇直捣敌巢周留城,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孙仁师、刘仁愿以及作为同盟军的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向加林城进发;刘仁轨则与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水军越过加林城,直击周留城。
刘仁轨部行至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时与四倍于己的倭国百济联军遭遇。这时刘仁轨麾下的水军包括170艘船只、2万人;日本和百济方面的水军包括800多艘船只、5万人,此外在江边还有百济骑兵作为策应。日本百济联军在兵力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不过刘仁轨也有自己的优势:唐朝的战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大型战舰,而日本船只则大小杂乱。刘仁轨的主要任务是运兵和押粮,事先他并没估计到会与敌军主力遭遇。开拔后的第二天刘仁轨在白江口外遇到了日本水军先头部队,双方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后就各自退去。这次战斗没什么决定意义,但双方都意识到:敌人的水军主力就在面前,决战即将开始。日本百济联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然而就是这次军事会议充分暴露出日本百济联军的弱点:参会的指挥官有百济王扶余丰璋、日本大将军阿昙比逻夫、前将军上毛野稚子、中将军巨势译语、后将军阿倍比罗夫......这些指挥官之间彼此并无节制,基本上是每个指挥官率所部各自为战。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将军们没考察水文风向之类的技术细节,而是在经过一番乱哄哄的讨论后得出一个极富乐观主义的结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这个结论用大白话说就是:我们一窝蜂冲上去就能把他们吓跑了。这样的作战模式其实和日本当时的国家性质有关:这时的日本其实还处于由原始部族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所以缺乏像已进入高度成熟的国家形态的中国那样一整套军队调度机制,日军实际上是由地方豪族的私家武装力量临时拼凑而成,之前从未有过协同作战的经验,所以很难在海上形成包围圈,倒不如大家一拥而上更为省事。这时唐军在纪律和训练上的优势就表现出来了:在中央舰队被迫后退收缩时两翼舰只利用相对靠前的局面同时向中央收拢。这样本来主动冲锋的日本百济联军舰队就陷入了唐军的包围之中。这时唐军舰只是顺流而下,而日本百济方面是逆流而上,水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唐军在兵力上的不足。
当刘仁轨发现自己的部队已成功合围敌军时立即下令两翼舰船同时夹击敌军。唐军除了用++向敌舰射击之外还采用火攻。日本百济方面数量众多的小船拥挤在狭小的水域内迅速乱成一团:夺路而逃的火船将火种带至后续大船。本来日本百济水军就布局混乱,这时就更为被动了。狭小的白江水面瞬间变成了下饺子的大锅,日本百济方面的士兵如果不想被煮熟就只剩跳水逃命这一条路可走了。这种局面进一步造成相近船只无法及时调转航向,日本百济联军已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随着唐军舰船不断向前推进使战争地点向河道宽阔的下游转移,配备火器的唐朝舰船成为实施攻击的主力。两天之内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此时的日军还没后世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战败后的日军兵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战争进行到最后地点进一步下移,转移到了白江入海口一带。日本方面册立的百济王扶余丰见大势已去就匆忙出奔高句丽,百济复国的梦想彻底破灭。《日本书纪》记载: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来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逆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日本将领朴市田来津是否死得如此壮烈已无法考证,但“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这样的记录恐怕是作为战败方的日本在战后的惨痛总结。《日本书纪》对由庐原君臣所率的第四批驰援部队的盛况也大书特书:“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在日本国内素有名将之称的庐原君臣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长途跋涉带来的一万日本青壮年竟是前来赶赴一场死亡之旅。
白江口之战堪称是国际版的赤壁之战,也可以被视为是东亚版的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希腊海军以三百五十八艘战船战胜波斯海军一千二百零七艘战船,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具备决定性国际影响的海战。相比之下白江口之战同样是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此次战役不仅是中日两国第一次交锋,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小龙虾性的战役。这是两国综合国力的一次较量:当时唐朝国力和倭国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武器战船存在代差,战术水准更是不在一个层次上。尽管在实际战场上日本方面占据兵力优势,然而唐将刘仁轨用火攻的方式几乎尽数将倭国战船焚毁。此战奠定了此后1000多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白江口之战使百济的复国之梦彻底破灭,至此唐朝开辟了针对高句丽的第二战场,此后大唐陆军继续从辽东方向攻击高句丽,而海军则从百济故地向高句丽发起进攻,可以说白江口之战为高句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同时白江口之战也遏制了日本向朝鲜半岛扩张的势头,而作为战败方的日本经此一役也充分认识到自身实力跟唐朝之间的巨大差距,进而采取了向唐朝积极学习的策略。此后日本不断派遣使者向唐朝学习:日本仿照中国隋唐王朝的三省六部制尝试构建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派出十几次遣唐使,中国方面也涌现出鉴真东渡这样的事迹。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甚至催生出一个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阿倍仲麻吕居留中国,取了汉语名字“晁衡”,还与李白、王维等人成为好友,他的后人自然就融合于中华民族之中;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也热衷于传播唐朝文化。
加林赛的部落的歌词
小龙虾
小龙虾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本站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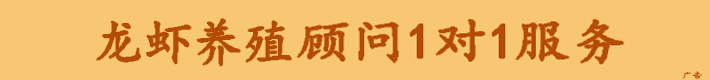


发表评论